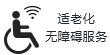合作化是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有效路径
发源于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的“新仓经验”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,在21世纪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,其演进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农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破解“组织化”难题的持续探索。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整合,到市场经济下的市场导向合作,再到新时代的数字化、全产业链融合,其核心始终是“为农服务”的初心与“改革创新”的勇气。
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,这一经验揭示了三个关键逻辑: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,让农户成为合作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,而非被动接受者;二是统筹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,既发挥政策的方向性作用,又激活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;三是推动生产、供销、信用深度融合,构建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合作经济体系。
当前,我国农业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、消费升级、全球产业链重构等新挑战,“新仓经验”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模式,更在于证明了“合作化”仍是破解“小农户与大市场”矛盾的有效路径。从平湖市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、落实“新仓经验”的实践中看出,联合合作是其改革的核心,市场化经营是主要方向。
事实上,农业市场化与农民组织化是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内容。
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,要推动“新仓经验”从“区域样板”走向“全国范式”,进一步强化制度供给,解决基层社登记注册、金融创新政策配套等关键问题。当合作化的阳光照亮更多乡村,中国农业必将在组织化、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,为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“中国智慧”。
01
“新仓经验”诞生的历史必然性:
破解“大国小农”困境的时代选择
人地矛盾倒逼下的组织化突围。我国农业长期面临“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”的严峻现实,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在面对市场波动、技术壁垒和自然风险时往往束手无策。以浙江平湖新仓镇为例,1950 年代初,单个农户在农资采购中因议价能力弱导致成本高企,农产品销售受限于渠道狭窄而价格低迷,周转资金更因缺乏抵押而困难重重。这种“小生产”与“大市场”的天然矛盾,催生了将生产互助组、供销合作社、信用社结合的“三角合同”模式 —— 通过生产合作整合劳动力和土地,供销合作解决购销难题,信用合作缓解资金压力。这一雏形本质上是对人地资源紧张、经营效率低下问题的系统性回应,开创了中国农业通过组织化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先河。
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改革逻辑演进。计划经济时期,“三角合同” 依托行政力量实现资源集中调配,既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统购统销,又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提供了稳定渠道,成为国家原始积累的重要支撑。改革开放后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生产力的同时,分户经营导致的 “小农户与大市场” 矛盾再次凸显:单个农户难以对接现代流通体系,技术采纳成本高,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。新仓镇在 1990 年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痛点,下决心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,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合联,从行政主导转向“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”,实现了从保障供应到服务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。这一转型不仅顺应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,更证明了合作化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上提升组织化程度的可行性。
政策驱动与基层创新的双向赋能。中央政策为“新仓经验”提供了制度土壤。自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“恢复供销社合作商业性质”,1995 年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》强调 “为农服务” 宗旨,2015 年中央11号文件要求供销合作社改革要“为农、务农、姓农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,提出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、供销合作、信用合作“三位一体”改革的宏伟构想。这些顶层设计为基层探索指明了方向。而新仓镇的干部、群众则在政策框架下展开持续创新:从“三角合同”解决短期购销问题,到 “农合联” 整合全产业链资源;从技术合作实现单产提升,到数字化管理推动效率革命。这种 “政策引导—实践探索—经验升华” 的良性循环,使“新仓经验”既符合国家战略导向,又扎根于农村实际需求,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“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”的典型范例。
“新仓经验”的核心内涵是“三维合作”重构了农业生产关系。一是生产合作:从分散低效到规模高效的效率革命;二是供销合作:从田头到餐桌的价值链条重构;三是信用合作:破解农业“融资难”的制度性创新。
02
“新仓经验”的时代价值:
破解 “三农”难题的系统性方案
资源整合的可复制方法论。“新仓经验”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“供销合作社搭台、企业唱戏、农户参与”的资源整合范式。在土地资源上,以产业农合联为载体规范土地流转,为土地碎片化地区提供了“组织化整合+数字化管理”的操作模板;在资金层面,通过资金互助会、银社合作等多元渠道破解融资瓶颈,其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员参与”的融资逻辑适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;在技术推广上,“科技小院+企业合作”模式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,各地可结合特色产业搭建类似平台,推动农业技术“最后一公里”落地。这种系统化整合思维,使分散的土地、资金、技术等要素产生协同效应,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底层架构支撑。
组织创新的层级化服务网络。从“三角合同”到“市—镇—村”三级农合联体系,新仓镇构建了功能清晰的组织架构:市级统筹资源对接外部市场,镇级整合产业实现规模服务,村级落地执行保障农户参与。以强村公司为例,其“职业农民承包制”培养了本土农业经营主体,数字化管理提升了生产效率,这种 “公司化运营+专业化分工” 模式可复制性强,为其他地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路径参考。供销合作社转型为“服务枢纽”后,整合政务、金融、物流等资源,成为连接政府与农户的桥梁,这一角色定位为基层组织改革提供了新方向 —— 从单纯的购销中介转变为综合性服务平台,增强对农户的凝聚力和服务力。
利益分配的公平可持续机制。“保底分红+二次分配”机制是“新仓经验”持续运转的关键。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获得稳定收益,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奠定基础;社员除按股分红外,还享受技术服务、优先收购等权益,直接提升参与积极性。这种分配模式平衡了集体、企业、农户三方利益:企业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,农户通过组织化提升议价能力,集体通过服务获取发展资金,形成“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”的共同体。在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、青壮年外流的背景下,这种机制有效激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,为解决合作经济中“搭便车”“分配不均”等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。
数字化转型的农业现代化路径。新仓镇的数字化实践证明,农业现代化并非依赖高投入的“智慧农场”,而是通过 “小步快跑”实现全链条升级。“数字农田系统”实现耕、种、管、收全程数字化,降低人工成本;“金服在线”平台打通农资采购与农产品销售线上渠道,解决了传统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。这些数字化工具并非“高大上”的前沿技术,而是基于现有互联网平台的本地化改造,适合不同地区结合自身产业特点推广。
在数字经济时代,“新仓经验”的启示在于: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农业生产、流通、服务流程,能够让小农户共享技术进步红利,实现“小生产”与 “大数字”的无缝对接。
政策响应与基层创新的结合范式。“新仓经验”的成功,本质上是 “政策红利+基层智慧”的结晶。从中央11号文件要求的 “三位一体”改革,到地方实践中“农合联”“强村公司”等创新载体,体现了 “顶层设计具体化、基层创新制度化”的互动逻辑。这种范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方法论:深入研究中央政策导向(如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、数字农业),结合本地资源禀赋(如产业特色、地理区位),鼓励基层开展 “微创新”,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。例如对接上海 “菜篮子” 工程建设长三角集散中心,既响应了城乡融合发展战略,又激活了本地农产品市场,实现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的双赢。
(孔祥智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专家监事,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二级教授、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;李欣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,全文详见第5期《中国合作经济》)